我对黄石国家公园知道多少?遗憾的是,我的认识几乎全部来自电影《2012》,在这部世界末日题材的电影中,黄石国家公园地底下的火山爆发,成为了引发世界末日的一个要素。而且,这部电影的发布也已经过去了大约15年。来到美国后,我对它的印象很始终很模糊,它似乎位列美国最具吸引力的几个自然景观之一。
去黄石国家公园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我就这样做了。起初,我打算看看在美国西部的拼车旅游的帖子(包括Reddit和小红书——平时我几乎不用小红书),但经过一系列徒劳的接触和等待后,我选择了独自参加旅行团,或者说“跟团”。对于真正的旅行者来说,参加旅行团未免是一种遗憾,而且这种旅行方式的利与弊也非常明显。但这对我来说,这是我前往黄石公园的唯一办法。
我规划了一个长达18天的旅行,这也是我做过的最长时间和成本最高的旅行。黄石公园及其周边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西雅图及其周边,第三部分是芝加哥和麦迪逊。规划如此长时间的旅行,一方面是想借一次出门尽可能多看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受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影响,希望能尽可能地做长程旅行。
我报的旅行团是一个主要由华人运营的针对华人游客的团。这里的“华人”是宽泛的概念,指的是所有具有中华背景的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他们可能是来美国旅游的游客,也可能是美国永久居民。理论上也可以有美国公民,但实际上这个旅行团里似乎没有。华人旅行团虽然表明是中英双语服务,但实际上偏重中文,因为车上不会说中文的人只有两个,而且也是亚裔。后来我在西雅图参加过一个一般性旅行团,里面没有华人,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这个旅行团的行程是从洛杉矶开始,但我选择在拉斯维加斯参团。由于旅行团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之间主要是赶路,所以我并没有错过什么东西。
目录
- 拉斯维加斯
- 从拉斯维加斯到圣乔治
- 下羚羊谷
- 马蹄湾
- 前往盐湖城
- 西黄小镇
- 黄石国家公园:老忠实泉和牵牛花池
- 在西黄小镇的晚餐与饮酒
- 黄石国家公园:诺里斯间歇泉盆地、调色板温泉
- 黄石国家公园:上瀑布、艺术家点、泥火山、西拇指、大棱镜、彩锅泉
- 离开黄石国家公园
- 大提顿国家公园
- 从杰克逊镇到盐湖城
- 告别
- 后续:在盐湖城的谈话,以及射击运动
- 离开盐湖城
- 结语
拉斯维加斯
置身于夜晚的拉斯维加斯的标志性街区Strip,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不就是现代的索多玛和蛾摩拉吗?”
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人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摆放着许多赌博机,这个城市在用这种强烈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风格。而这诚然是我不喜欢的风格。
9月26日晚,我抵达了拉斯维加斯。经过一次转机以及总共七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在离开机场时疲倦不堪,不再想研究公共交通线路,而是直接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我预定的Airbnb。在车上,我跟司机聊起了这座城市,他说,人们来到维加斯,只是知道Strip,只是去赌博,但是维加斯还有其他好东西。我问他还有什么好东西,他谈起了维加斯附近的自然景观,从东可以去大峡谷,向北可以去黄石。
在Airbnb安顿下来后,我打起精神,步行前往Strip。中文世界也把这称为“赌城大道”。由于第二天下午我就要搭乘前往黄石公园的大巴车,所以这是我观看这座城市夜景的唯一机会。Strip这边的行人熙熙攘攘,但总体上却并不显得喧闹。大型豪华酒店、赌场和街道上的棕榈树,便构成了Strip的特征。
我也远远地看到了维加斯的埃菲尔铁塔,但没有走近参观。这立即使我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电影主角在《2012》从拉斯维加斯起飞时,飞机撞到了埃菲尔铁塔。当时我就没弄明白这件事,还以为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飘到美国去了。


在主干道走了一会儿后,我拐进一个巷子,走向摩天轮。这个巷子显得更有正常的烟火气,而并非维加斯独特的纸醉金迷的腐烂气氛。

逛了一会儿后,我乘坐公交车回到住处,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29分。我收拾了一会儿后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跟房东沟通好以后,把行李箱收拾好放在客厅。9点52分,我出发前往Strip。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在思考这座城市的宗教情况。如果这座城市如此“堕落”?那么这里有多少人信仰宗教?这里的基督教团体是否会感到尴尬?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并不认为道德必须要由宗教来维持,但是宗教可能也是有用的。而我的确也在这里的街头看到了基督教的广告人员。

我在附近的一个大型人行天桥上逛了逛,发现对面街上有一个博物馆叫做Museum of Dellusion(幻觉博物馆)。我没有时间进去参观,而且收费不低,但这倒是很符合我对拉斯维加斯的印象。
我站在天桥上时,两位打扮成棕榈树的女士走到我面前,问我想不想跟她们拍照。我习惯性地礼貌地拒绝了。她们的询问带有某种挑逗的意味,因为她们一边问,一边用手触碰我的臀部。
许多人知道在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性交易是合法的。不过,这其实仅限于内华达州的一些合法妓院,而且拉斯维加斯没有合法妓院。所以,性交易在拉斯维加斯是非法的,这也许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尊严”。

我没有多做停留,而是乘公交车前往城市北部的Fremont Street。据说这里的知名度要仅次于Strip,而且这里有一个步行街叫Fremont Street Experience。我看到这里的一些酒吧的吧台直接开设在步行街上,面向行人。当然,这里也免不了有很多赌场。

由于拉斯维加斯的总体调性跟我不符,我在准备离开时并未带有一点遗憾,尽管我只待了很短的时间。我乘坐公交车回到住处取回行李,在一家快餐店吃了午餐,便打Uber前往黄石旅行团的集合之处。我抵达那里时才发现,这也是一个大型酒店和赌场,我在走向集合点的路上必须穿过一个巨大的赌博厅。

在集合点,我看到许多拉着行李箱的华人面孔的人。我跟一对夫妇简单聊了下,得知他们也是去黄石公园,但跟我不是一个团。在预定集合时间不久后,我等来了我的导游,他叫Ethan,是一位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他引导我登上了旅行团的大巴。
我的位置旁边坐着一位来自上海的大叔。我和他都是一个人参团的,不过我当初在找代理商报名的时候搞错了价格,以为我一个人报名也可以享受拼团价,这使我一度陷入犹豫。代理商后来问我说,有另一位男士独自参团,要不要两个人一起报名?两个人一起报名的价格要比一个人报名的价格低三千多人民币。我当然选择了两个人一起报名。
从拉斯维加斯到圣乔治
满载55人的大巴车出发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团旅行了,我依稀记得上一次跟团旅行还是2017年我一个人去四川和云南交界处的泸沽湖之旅,而跟团的确是最便利的前往泸沽湖的方式。
一般来说,美国的服务业人员的交谈技能和服务态度要比中国的服务业人员要好,所以Ethan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导游,这也就不奇怪了。我第一次跟团旅行是2010年去九寨沟,那位女导游的脾气非常暴躁,骂游客们购物太少。
由于行程从拉斯维加斯才算正式开始,所以Ethan也开始介绍起了相关的事项,包括他们公司、这辆大巴和相关注意事项,等等。他说这辆车的价格是80万美金,相当于三辆劳斯莱斯。他不愿意乘客们使用大巴后面的卫生间,说可能会让后排乘客感受到异味,但我想可能是因为清洁卫生间的马桶收集箱需要一些成本和时间。
这一天接下来仍然是赶路,从拉斯维加斯赶到圣乔治。我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看风景——但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视野不佳——和跟旁边的大叔聊天。他谈起了自己女儿的情况(比我大一岁),在中国读本科,在美国一所大学读硕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现在在西雅图远程上班,而公司不在西雅图。她工作轻松而薪水丰厚,这在国内根本不可想象。即便如此,据说她还是有以后回国的打算。“我跟她说,你千万别回来。”很快,他谈起了中国的一般性情况。虽然我感受得到他接收信息的渠道相对有限——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我和他在许多议题上观点接近。
由于我没有直接明确发表看法,他在说完后以一种保险的态度说自己这个年纪认识到了很多事情,而我不一定能注意到。
同时,大叔也是一位真正的摄影师。他带了一台单反相机,但或许由于使用不便,或许由于快门键有问题,他主要是在用自己iPhone来拍东西。他喜欢说,手机够用了,而且有时候会更好。
由于我坐的位置不方便拍照,所以在车上时我一般没有拍什么东西。而大叔则经常举起手机拍照片或摄影,并且现场就把它们修好。


从拉斯维加斯到圣乔治的15号州际公路路上,景观相对单调,主要是荒漠。在路过一个河谷路段时,导游说这是美国每英里造价最高的高速公路,并解释这是由于施工难度大、美国工人“懒惰”和人工费用高昂。我在撰写这篇游记时查找资料,发现这个维尔京河峡谷(Virgin River Gorge)路段,在1973年建成时的确是当时美国造价最高昂的乡村高速公路,但现在应该已经被其他工程所超越了。
在1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我开始强烈地感受到我的自然地理知识的匮乏,尤其是缺乏地质学和植物学方面的知识,这使我的旅行和写作都备受掣肘。如此匮乏的知识,对于两百年前年的旅行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歌德在游记里就很擅长地谈到岩石和植物。Ethan的介绍也很简略,他提到这里过去是海洋,而这里的岩石的形态则是过去的结果。
同时,Ethan也给我们播放一部纪录片,叫America: The Story of Us。主要是讲述美国历史,我发现它制作得很好,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晚下榻圣乔治,而我们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大巴先开到一家大超市去让大家采购物品、晚餐和第二天的早餐,随后便开到一家汽车旅店。Ethan一再提醒我们,第二天早上六点必须出发,否则无法按时感到下羚羊谷。由于抵达旅店的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1分,所以我很快就休息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美国的旅店,因为此前出行都是住Airbnb。房间内部的情况要比从外面看要好。
这一天我注意到同行的一位女子,她似乎是一个人出行的,看起来像是本科生。她的个子很高,身高可能至少有1米78,反正明显比我高,而且总是戴着一个棒球帽。在我最后一次进入自己的房间时,看到她站在外面打电话。接下来我还会提到她,这里叫她“小姑娘”吧。
下羚羊谷
第二天,9月28日,早上六点出发时,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天蒙蒙亮的时候,大巴正在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行驶,地貌仍然是荒漠,同时视野非常辽阔。此时让我想起2015年我在西藏旅行的景象,当时我因为能看到极远处的山峦而震撼不已,但这里同样也能看到。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车内时,我看到大巴车里的许多人正在睡觉,有人不耐烦地拉下了窗帘来挡住阳光。我基本上保持了清醒,因为我前天晚上睡得比较早。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大约在当时时间上午八点抵达了下羚羊谷(Lower Antelope Canyon),导游在买票后,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和排队后,开始向下羚羊谷前进。也许同行者们或多或少知道下羚羊谷是什么样子,而我有意地拒绝查看这里的任何资料,而是带着一种一无所知的状态来到这里。
在等导游把各种事情安排妥当的过程中,我在外面听大叔给我讲摄影知识,以及他的西藏之旅。这时,一位独自来自芝加哥的永居美国的大妈来到我们这里,也来找大叔讨教摄影知识,同时也希望他能帮忙给自己拍照。她先是谈了谈自己的人生观,说到了这个年龄就是应该出来玩,不要害怕出什么意外,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
“咱们旅行团里的人的素质真高”,她看着我说,“你看,还有博士。”实际上,她的一个儿子也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生,而且学的不是我这种“没用”的专业。
我说,现在能来美国旅游的人可不是什么一般人。毕竟,它们要么是居留在美国的人;要么愿意在这个航班架次远未恢复正常从而花费高额票价的时期来美国旅游的人,而且还要持有美国签证。至于我,则简直不值一提。浙江大学在华人眼中也许是块亮眼的招牌,但在美国算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没觉得自己算老几。

进入下羚羊谷时,同行者们分成3个组,每个组会有一位印第安人导游,先缴纳每人3元的小费。下羚羊谷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地盘。在经过一段陡峭的下降的梯子后,我们进入到谷中。这里非常狭窄,所以一个人走在谷中,前后都有人,不能过多停留,否则会阻碍全部进度。


游览的总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其中的体验则有些复杂。由于前后都有人,到处都传来人的声音,所以并不能很好地沉浸在周遭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师,所以许多人实际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通过屏幕看景色。我怀疑,摄影已经让旅游变得有些“异化”了。
我们所置身的世界是一个由紫粉色或橙色的纳瓦霍砂岩包围的羊肠小道。我不停地听到周围的人惊叹“太美了”,但我自己却没有这种强烈的冲击感。如果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也许会有不同的体验——但这是不可能的。
羚羊谷是由纳瓦霍砂岩被侵蚀而形成的,而纳瓦霍砂岩只是分布在美国西部的一些地方,所以羚羊谷这种景观是美国独有的。羚羊谷虽然在华人圈的名气很大——这主要是旅游公司的助推——但在美国却不算十分重要的自然景观,所以一般来说是作为前往黄石或附近其他自然景观路上的一个驻足之处。
有同行者说,走在这个谷里,随便怎么拍都是好照片。但是大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一方面他认为,这个谷已经被人给拍“滥”了,所以自己再拍也没有太大意思,另一方面,他认为要在这里面拍出好照片还是很有讲究的,尤其是光线的问题。而我自己也感到,无论是这种商业的批量化的跟团旅行,还是这种已经被人走得太多的地方,也很难写出好的游记。



同行者中的几位大妈显然很急切地在找别人帮她们拍照,而我自己没有太大的需求,只是在导游接连帮大家拍照的同时,自己也凑上前去让她拍一下。导游也是拍照的好手,她们会用手机的全景模式来拍摄,但可能仅限于iPhone。我的那位导游不大会用我的相机,也显然玩不转我手机上的Google相机。这也不是她的原因,因为Android用户在美国是弱势群体。
有次,一位大妈急切地让那位小姑娘帮她拍照,而小姑娘自己还忙着呢:“等等,我还要拍呢!”要不是我隔得有点远,就凑上前去帮忙了。过了一会儿,小姑娘走在我的前面,我主动问她是否需要帮忙拍照,她礼貌但也并非热情地拒绝了,而是让导游来拍就好了。好几位大妈也请我帮她们拍照。小姑娘也很乐意用英语跟美国人交谈,虽然有次一位引导员是对着我问了一个问题,但她抢着回答了。
走出羚羊谷后,我们在走回游客中心的路上,小姑娘显然依然兴致勃勃,找一位同行者帮她拍照,而她坐在地上,举起双臂。我顺手也拍下了这一幕。

回到大巴车上后,Ethan说把另一组人的消费给要回来了,据说它们分配的印第安人导游态度不佳,也拒绝给她们拍照,因为嫌他们走得太慢了。同时,据他说,几年前,有中国游客在谷内的岩石刻了“XXX到此一游”,这很快导致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在谷内,不能背包,不能录像。
马蹄湾
离开下羚羊谷后,大巴车驶向马蹄湾(Horseshoe Bend)。同样地,我并不知道马蹄湾是怎么回事。Ethan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会在河边走。我们在10点5分离开下羚羊谷停车场,在10点23分便抵达了马蹄湾停车场。Ethan只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这包括我们走到马蹄湾和走回停车场的时间,而单程路上就要走十多分钟。
此时游客就很多了,步行道上挤满了各色游客,等我走到观景处时,发现那里也挤满了人,这时也才发现这是一个俯瞰科罗拉多河的高处,而不是河边。


由于大约只有半小时的驻足时间,我也仅限于在观景台附近看看,而不能走很远。这个观景处的确是观察这里的辽阔地貌的最佳位置。我们所处的地面距离下面的科罗拉多河大约有300米,如果不小心从这里跌落下去,当然就没有活路了。站在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面上有游艇和皮划艇正在行驶。这些人是怎么下去的,就无从知晓了。
之所以叫马蹄湾,是因为这个蜿蜒处是马蹄状的。



我是和大叔一起抵达观景处的,但我和他很快就走散了。随后我一个人在悬崖边缘走动和观看着河谷的情况。小姑娘发现了我,让我帮忙给她拍照,于是她坐在悬崖边,背对着我,举起了一只手。她似乎很喜欢用这个姿势拍照。拍完后我顺便让她帮我拍两张,她答应了,不过此时另一位同行者Jay来到我们这里,同时又有其他不认识的来自欧洲的游客站在同样的位置拍照,所以我们等了一会儿,而我也跟Jay攀谈起来。此时,小姑娘不想等待,直接溜走了。
Jay让我帮他拍照,我拍完后让他帮我拍。他也是一个人参团的,并且居留在美国。他住在芝加哥,这次是先自驾开车到中途某个我忘记名字的地方,再坐飞机来参加这个团。他没有考虑自己自驾游黄石,是因为路程太长。同时,他自己也有相机玩摄影,但是这次没带,并且也给我传授了摄影经验。
我和Jay一起走回了停车场,中途聊起了美国其他地方的旅游资源。他向我推荐阿拉斯加,说12月正是合适的时间。
前往盐湖城
11点40分我们从马蹄湾停车场出来后,大巴车在附近的佩吉市的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让大家吃午餐,我去了我最忠实的麦当劳。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是继续赶路,中途路过一个加油站和一个纪念品店(这家店给旅行团打八折)。这个下午对这篇游记来说,可说是一块留白的地方。
趁这个机会,我想再就那位小姑娘多说几句。我迅速地注意到她,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是旅行团里为数不多的跟我同年龄段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她的性格似乎跟我惊人的相似。她喜欢单独行动,自己走走,这儿拍拍,那儿看看,不怎么主动跟人谈话,但是也会微笑着听别人谈话或善意地观察别人,而并不害羞。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容易察觉到同类,并且把她归入到某种archetype中。
旅行团里还有两位同龄人。她们说自己是好莱坞那边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我没有详细询问情况,但听起来非同一般。由于她们是两个人一起来的,所以她们大多是在进行内部交流,说一些其他人无法参与的话题。
晚上8点我们才抵达盐湖城。在快要进城的路上,一轮圆月突然出现在远处的两座山峰之间,许多人惊叫不已。这个时刻颇为特殊,它在北京时间已经是中秋节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中秋节前夜。
Ethan安排我们在一家自助餐店吃晚餐,然后把我们拉到一家颇为豪华的酒店。我和Jay一起吃晚饭,他提到自己是因为父母移民才过来的,而将来自己还是可能会回到中国生活,因为父母养老更方便。他还提到了目前移民美国的趋势,以及一些美国大学互相不承认对方学历的现象。他还提到,美国的物价自疫情以来上涨严重,而且没有下调的趋势。这次的自助餐价格23刀,但在几年前可能不超过10刀。
我拍了一张月亮的照片,配上文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误)”发给一位在中国的朋友。显然,写下这个诗句的唐代诗人张九龄没有时区的概念,因为中国现在是白天。抵达酒店的时间是9点31分,我很快就休息睡觉了。
西黄小镇
9月29日早上,我和大叔一起在狭小的酒店餐厅用完早餐后,登上大巴。我们本来是坐在第三排,但从这天开始,Ethan把我们调到了倒数第二排。大巴离开时间是早上7点40分。登车不久,大叔正在手机上看许家印被捕事件的新闻,他一边用手指指指点点,一边用上海普通话点评,其中提到恒大在上海的烂尾地产。他的上海普通话我也并不是每句话都能听懂。
我们前面也坐着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他很快就用上海话跟他们讨论这件事。同行者们有一些上海人和一些广东人,他们在内部交谈时会换用上海话和粤语,这两种语言都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中途在一家加油站兼旅游中心停过,地名叫Flying J Travel Center。我和大叔各自跟这辆豪华大巴合了个影。这辆大巴的厂家来自加拿大,型号可能是H3-45。
司机是一位香港背景的华人,每次到达一个地点下车,他都会站在门边,一只手依靠着车皮,一边向每一位下车的乘客致意。Ethan说他是行业标杆。不过他一直做着这个默默无闻的工作,以至于我都忘记了他的名字。


大巴在逐渐接近黄石公园时,周遭的自然景观开始发生变化,由荒漠和低矮植物构成的世界逐渐变成森林,不时看到河流在森林中穿行。这种景观的变化使我预感到重要的事物正在到来。
Ethan开始警告说,接下来两天在黄石公园都没有信号,让大家先给家人说清楚。一位同行者Sunny把自己的微信昵称加上了一个后缀“(30号、1号没信号)”。但实际上西黄小镇是有信号的,而黄石公园内部的确大部分区域都没有信号,而没有信号当然未必是坏事。假如这是个中国景区的话,信号可能遍地都是了。

下午1点2分,我们总算在西黄小镇(West Yellowstone)下了车,Ethan径直带我们走进了一家中餐馆。——顺带一提,他会说“今天中午/晚上我带大家去吃……”,不过只是推荐,而不是强制的。
吃饭时,大叔、芝加哥大妈、我和另一位小伙子坐在了一起。小伙子只是我一开始的初始印象,后来我得知他已经年过四十。他叫Rex,来自广东,在深圳工作,从事的是康复行业。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点了鸡肉、牛肉和——鹿肉!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鹿肉,但它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对食物并不是特别敏感。
芝加哥大妈谈起,自己当初从上海来芝加哥,是因为她本来是东北人,但是在上海的时候没有户籍,孩子没法入学高中,于是只好“背井离乡”,来到芝加哥。在Rex和我看来,这个“背井离乡”用得过于喜感。至少在我看来,当初这件坏事反而成全了一件好事。Rex介绍自己原先在公立医院工作,并谈了谈自己从事康复行业的情况。大家可能还讨论了中国最近的经济形势,这是现在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黄石国家公园:老忠实泉和牵牛花池
大家用餐完毕后,我们的大巴进入黄石公园。在进大门的时候,Ethan提到,今天是中秋节,但由于人在旅途,自然就对这个节日没有什么感觉。一般而言,我也没有什么思乡之情。进公园大门后,手机很快就没有信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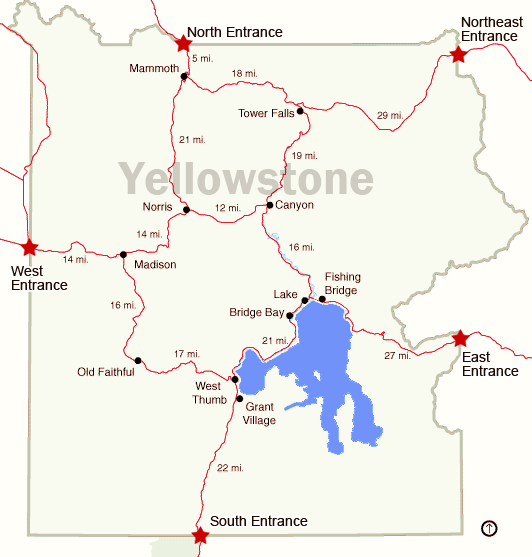
大巴径直前往老忠实泉(Old Faithful),中途路过了大棱镜(Grand Prismatic),但中途没有停留。Ethan开始隆重给我们介绍黄石公园的情况,这包括,它建立于1872年,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等等。Ethan开始称赞当时这种理念之先进,同时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所以联邦出面来管理某些重要的景观,而黄石公园又跨越了州界。这在美国这一政治实体中似乎很显而易见。(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设立于2021年)同时,Ethan也介绍了公园里的动物们,主要是牛、熊、鹿和狼,尽管我们几乎只看到了牛。他也提到了黄石公园的火山爆发的可能性,并且从宏观尺度来看现在黄石公园火山正在喷发的窗口,但这也许在近几百年内不会发生。
在前往老忠实泉的路上,我们就已经能观赏黄石公园的景色了。路途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河边行进,先是Madison河,后来是Firehole河。公园里的树种分布茂盛,同时种类相对单一,大多数都是扭叶松(Pinus contorta/lodgepole pine),由于这一树种四季常青,所以公园里现在很少有树正在变色或落叶。
老忠实泉附近开发得很完善。有一座巨大的像城堡一样的木制的酒店建筑坐落在附近,据说这里的房间要提前两年预定。喷泉的附近建成了一个半圆形的看台,我们抵达这里时,看台上的座椅已经坐满了人,许多人站在后面。而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典型的“美国现象”:人很多,但却很安静,一方面是因为天地辽阔,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人习惯了在公共场合不大声讲话。一旦有人大声讲话,人们隔很远都能听见。

老忠实泉之所以叫老忠实泉,是因为它是一个可高度预测的间歇泉(geyser),每44分钟到2小时喷发一次。
我们的等待时间大约是20分钟,等到预定的重新集合时间它都还没喷发,我就开始往集合点走了。这时,它经过漫长的酝酿,终于喷发了。在喷发之前,偶尔也有少量的滚烫的泉水喷出来。遗憾的是,我的照片无法把它喷发的博大气势记录下来,而只能用手机拍摄视频的截图。有其他观看者称,这次喷发还算盛大,至少有30米高。只见泉水先是以水柱的模样喷射到高处,再在空中以波涛的状态向四周喷涌。老忠实泉的确名不虚传。

在回到集合点后,我们要徒步走到一个叫牵牛花池(Morning Glory Pool)的地方再走回来。在我看来,较长时间的徒步才是自然旅行的真正重要之处。路途都是修好的道路或木质栈道,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度,起伏不大,而且往返只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美国人显然抓住了自然旅行的精髓,所以美国到处都设计有Trail供游人行走。Ethan提到,中国的许多景区都被过度开发了,大修栈道,而美国的许多Trail的理念则是尽可能保持原生态,只是在现有的土地上腾出一条路。
我们行进的步道叫Upper Geyser Basin Trail。在路上,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间歇泉或水池。间歇泉都在沸腾,并不断冒出白色水蒸气,而有的还在喷发。而水池的颜色则五彩斑斓。



这里的景色的确让人心旷神怡。这让我想起了北疆,虽然我没有去过,但看过图片和小说。有一段时间,Rex在跟我一起走,他也提到,除了这里的间歇泉和水池,这里的景观跟北疆是很相似的。黄石公园的泉是世界罕见的。
在与同行者们交谈时,大家都很容易地谈到自己去到过的某些地方跟黄石公园的某些地方的相似性,这应该是旅行的当下场景牵动了过去的记忆。与我以前遇到的人不同,这里的同行者们谈论的地方包含了全世界各处,有两位大妈很喜欢谈论土耳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北疆、西藏等不太容易去的地方。如果你在中国而来美国旅游的机会渺茫的话,那么可以在新疆和西藏等地找到类似的景观。




牵牛花池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水池,而这里的看台已经挤满了游客。水池的颜色是由生活在水池的细菌导致的。关于这个牵牛花池,最著名的故事是有游客往里面投掷物品(据说主要是硬币)导致了堵塞,使得水池的颜色不再那么鲜艳。Ethan的说法是,经过清理后,水池的颜色反而变得更好看了。我查找了各个时代拍摄的照片,发现在60年代及其之前,牵牛花池的中央的颜色不是现在的绿色,而是蓝色。
返回的时候并不是原路走栈道,而是走更近的公路。在一个河流蜿蜒处,很多人下去拍照。一位大叔想给自己老婆拍照,但是几位年轻人迟迟没有把位置让出来。他不耐烦了:“你们拍了就不要拍了,我给我老婆拍几张。”这几位年轻人听见这个有秀恩爱嫌疑的话语,连忙一边打趣一边把位置让开了。
回到车上后,我发现我的手机有信号,但我旁边的人们似乎都没有。于是我开了个热点给大家分享,我的热点名字叫“FBI Surveillance Van”。似乎坐我后面的大叔真的以为我是FBI,不然怎么唯独我有信号?我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我的运营商恰好有信号,但我其实对信号没有什么依赖。
此时天色渐暗,Ethan说我们走得太慢,耽误了时间。实际上,我觉得这已经走得够快了。跟团旅游就是这样,一切都要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在徒步行进时没有太多停下来流连忘返的余地。无论如何,这导致当天原本要去大棱镜的规划只好取消,因为据说此时拍不出什么东西了。
在西黄小镇的晚餐与饮酒
回到西黄小镇后,大巴在另一家中餐馆附近停了下来,此时许多同行者已经意识到大家其实可以不听他的推荐,所以大部分人径直自己到小镇里找吃的。我个人也认为,既然人来了美国,就不要太留恋中餐了。
我和大叔本来在找吃的,同时Rex和Sunny也加入其中。大叔打算去吃麦当劳,而我此时正对麦当劳感到腻烦,所以决定加入Rex和Sunny,前往小镇中心探索。在走向小镇中心时,我又遇到了那位小姑娘,它有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似乎好奇我们要去哪儿。
这时我第一次注意到Sunny。由于之前Rex给我提到了一位“姐姐”,我以为他指的是这位Sunny——实际上他指的是芝加哥大妈——于是我问Sunny:“这位姐姐也是广东人吗?”而她的回应让我始料未及:“你怎么叫我姐姐,难道看起来我比你大吗?”我意识到自己不慎触碰到一个雷区,连忙说:“我……22岁啊,难道你比我小?”她说:“我18呢!”
在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找到了一家烧烤店,有很多人排队,店里的少数几张座椅根本不够坐,所以很多人时打包带走。这里的肉的确不错,让我意犹未尽,但我点菜失误,导致我没有吃完。跟我们三个坐一起的是旅行团里的另外一对母子,由于母亲看起来很年轻,所以不容易判断出他们的关系。他们居留在美国,来自纽约,而原本来自福建。听说福建某些地方的女性在很小的时候就会生孩子。
回到大巴车上后,大巴车先是把我们拉到一个超市购置物品。Sunny和Jay正在酝酿晚上一起喝酒,还问我要不要一起,我欣然答应。旅行团把我们分派到三个不同的旅店,由于一些沟通失误,Sunny和Jay跟我和Rex分开了。费了一番周折后,我们终于在Rex的房间里碰面了。参加这次饮酒的人包括Sunny,Jay,Rex,一位姓曹的广东人,一位我忘记姓名的在美国居留的台湾大叔,和我自己。
我还擅自邀请了两位在好莱坞的音乐学院学习的两位女生,但她们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且也没有参加。我还询问了上海大叔,他不参加,因为他似乎不喝酒。我还像询问小姑娘,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
Sunny这次出行颇为不顺。她是广东人,但一直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她没有赶上香港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于是临时买了当天飞纽约的飞机,再立即飞到美国西部。她先是在美西游玩了一番,又参加了我们这个旅行团,然而某些行程是重复的,其中包括下羚羊谷,所以她没有跟我们去下羚羊谷。由于刚刚的沟通失误,导致她没有跟我们住在一个酒店,于是她一抵达,沮丧之情就写在了脸上。但既然是喝酒,一旦气氛起来了,她的情绪也很快融入其中。通常来说,喝酒并不是一个情绪调节的好办法,但社交是。Sunny成为了我们谈话的焦点。Rex一边拿Sunny打趣,一边说以后可以带她去南美玩,只要跟着他走,就不会在行程上出问题。
曹先生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一位在酒桌上善于添加欢乐气氛的人。他跟妻子一起来旅游,而他的妻子看起来温文尔雅,并不参与饮酒。他在介绍自己的称呼时,由于故意或非故意发音不准确,把自己的“曹”的二声说成了四声,变成了“操”。“Mr. 操”,他说。我听到这个,跟Sunny笑了很长时间才缓过神来。他听说Rex从事康复行业后,便称呼他为“妇科主任”。同时,这位曹先生也有着典型的中国社交风格,他建议大家建一个群,以后遇到可以相互照应。
台湾大叔说自己的父母在1949年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而自己很早就已经来到了美国。他跟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中国认同”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在美国,其他人也是把他们当成中国人看待。他的妻子好像从事酒的销售,所以很懂酒,在曹先生谈论美国的酒的口味时,对他的看法表示认可。
Jay和我一样,似乎在酒桌上相对沉默。而我暗自感到有些惊奇,因为我们这些人才刚刚认识,但仿佛已经互相熟识了一样。Sunny坐在我旁边,当他听闻我的专业是历史学后,说自己也很喜欢历史,尤其是看欧洲的历史遗迹时对它们背后的历史很感兴趣。Sunny在香港做投资行业。在我看来,这对他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一种高雅的趣味。她还会讲四川话,但不愿意直接表明自己为什么会讲。
我发现,一旦许多人听闻我的专业是历史学这个没用的专业后,便会停止一种世俗的找工作或就业的视角,而是来谈论一些有趣味的而无利害的东西。
中途,导游Ethan也加入了我们,他谈到自己之前在中国是“吃皇粮”的,关于这个词的意思,大家就只能自己猜度了。
这次饮酒活动中,许多谈话内容是相互取笑,以及谈论一些跟酒、美国风光、接下来的行程相关的日常话题。
我喝了太多的酒,啤酒加红酒,也许在曹先生给我倒酒的时候,我应该更坚定地拒绝,并且谨慎地评估自己的酒量。过了晚上12点,这次饮酒活动结束了,此时我感到有些难受,连忙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洗漱的时候发生了轻微的呕吐,同时也头晕目眩。这可能是我喝得最多的一次。这时,大叔也还没有睡。很快,我上床休息了。
黄石国家公园:诺里斯间歇泉盆地、调色板温泉
9月30日醒来后,我发现我的身体状况不佳。从头到脚都不舒服,尤其是胃痛,脸色似乎也是苍白的,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抵达拉萨时发生的高原反应。这应该是过量饮酒导致的,但同时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流感或COVID-19。
这对我接下来的旅行是一个重创,胃痛是最不利的。如果你读过隆美尔的《步兵攻击》的话,就会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亮相之初饱受胃痛的折磨,这严重影响了这位当时的少尉以及未来的元帅的首次发挥。我在旅行时感到胃痛,便立即想起了隆美尔。
这一天都是在黄石公园,在一个又一个景点之间奔波,每个地方都没有停留太长时间。实际上,我在撰写这篇游记时,也没法立即凭空回忆起去过的每个地方,这很有可能是我当时身体抱恙导致的。所以,写游记也是我搜寻和重整记忆的一种办法。这个旅行团在代理商那边的广告标榜的是“深度游”,但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深度。真正的深度游应该自己开车来,并且停留至少四五天时间。
早上遇到Sunny时,她给我起了个外号“22岁”,并这样称呼我。她说自己前天晚上只睡了大约四个小时,因为酒店房间不太令人满意,不过她的精神看起来是很不错的,至比我要好。

我们去往的第一个地方是诺里斯间歇泉盆地(Norris Geyser Basin),各种大大小小的间歇泉释放出来的白色水蒸气笼罩着这个盆地。如果站在水蒸气中,味道并不好闻,据说那是硫磺的味道。我们要从山上走到盆地,在盆地的步道里走一圈,再回到山上。



我身边的同行者们已经开始议论说,对这样的自然景观开始感到审美疲劳了。我注意到那位小姑娘也不再怎么找人帮她拍照,而是自己竖着手机录像。Sunny和Jay开始组成一对拍照组合,互相给对方拍照。而我和他们两人都穿着红色冲锋衣,所以Rex叫我们三个人“红衣主教”。
在我走回山上时,我注意到那位小姑娘和一对来自杭州的母女走向了一个分岔路。我看表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也跟她们走了过去。看路标说是通向一个观景台,但走了一会儿连观景台的影子都没看到,于是走在我前面的小姑娘中途折返。这样,我们就相遇而行了。我按照通常的美国礼节,微笑着说了声“Hi”,她同时带着她特有的天真表情对我说了一个两个字的词。
这个词是什么?我认为我听到的是“哥哥”,但也许由于这个称呼太罕见、太不可思议,我隔了一秒多的时间才反应过来,惊讶地回过头看她,而她似乎刚刚也在回过头看我。接下来,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听错了。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用普通话这样称呼我,而且是来自这样一个似乎不大主动跟人交流的人。在四川话里,如果有什么人叫你“哥哥”,她很有可能是准备开始骂人了。她真的说的是“哥哥”吗?也许下次碰到她我可以直接问这个问题,但似乎不是很合适。但无论如何,我的心在那一段时间融化了。看来我要继续调整我对她的archtype。
我在走到一口沸腾的大锅那里后也折返了。在这之后,我感到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胃痛也越来越明显。回到车上后,坐我前面的上海夫妇十分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嘘寒问暖,也许是因为我的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

下一站是调色板温泉(Palette Hot Spring)。停车场离要去的地方很近,但这段路程我却走得十分艰难,这种艰难的状况很明显影响了我感受景物的能力,也减轻了我试图举起相机的尝试。无论如何,Ethan只给了我们很短的时间,只供我们走到一个栈道处,停留一下看看拍拍,再走回来。在调色板温泉可以看到从白色到黄色的各种岩石,以及覆盖或流淌在上面的泉水,总体上,目前它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


这里的栈道人很多,虽然栈道很长,但拍照还是会出现等待别人腾出位置或者等人先通过的现象。
大巴车在某个地方的卫生间停靠过,让大家使用卫生间。我在车外面等着时,两位路过的手拿咖啡牵着狗的美国(白)男人看着我们这群人,说了句:“Chinese Communist Party”。看来大家最好要对自己国家和民众在其他国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要有自知之明,虽然自己未必助力于建设这种形象。
黄石国家公园:上瀑布、艺术家点、泥火山、西拇指、大棱镜、彩锅泉
此时已是中午,大巴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Canyon的游客中心吃午餐。
这一路段的景色非常优美,但可惜我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此时正值中午,阳光正好,道路两边都是平缓的草原,偶尔能看到落单的牛在吃草,有可能还看到了野马。Rex坐在我附近,他说,像这样的地方,最好的方式是找个湖边坐下来喝一下午咖啡。我深感赞同,而此时我感觉自己正坐在一个飞驰的牢笼里。这里是整个公园的北端,人迹罕至。也许每一个生活在城镇的人都有一个隐居的梦。不过,Ethan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的方式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旅游,而不是像美国人一样以chilling的方式来旅游。而我认为后者才抓住了旅行的要义。
抵达游客中心时,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我申请就留在车上睡觉,但是司机先生不允许,一方面车要关门,另一方面乘客的财物都还在车上。大叔,一位我忘记来历但是居留在美国的大妈,和我,一起前往一家美式烧烤店。由于导游推荐了这里的牛肉,所以我们都点了这里的经典牛肉汉堡。我还点了一杯可以让我续命的咖啡。
这位大妈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跟丈夫一起来的,他们在大巴车上就坐在我们后面。不过她的丈夫胃口不好,就没有来吃饭。大妈谈到了自己的儿子本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建筑,现在正在剑桥大学读AI方面的研究生——按照华人的排名习惯,这样的履历差不多已经到人生之顶了。所以,她谈到,他们出去旅游经常是去看建筑。在这次旅程中,他很乐意介绍自己并未到来的的儿子。
大叔谈到了他去西藏的旅行,他和其他一些朋友,包了个大巴从上海开到西藏再开回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还在那个大巴上做饭。由于路线都是自己制订的,所以这样的旅行方式在我看来也非常不错。
喝掉那杯美式咖啡,的确让我感觉好了一些。
行程继续,接下来是前往上瀑布(The Upper Falls)和艺术家点(Artist Point)。


上瀑布是黄石河的一段狭窄和湍急的河段,瀑布的落差为33米。河水蔚蓝而清澈。遗憾的是,虽然我们观看的地点就在瀑布的正上方Brink of The Upper Falls,但是它恰好不是观赏这个瀑布的最佳地点,因为这里虽然能近距离感受到瀑布的力量,但是却看不到它的全貌。网络上找到的关于这个瀑布的图片并不是从这里拍摄的。
艺术家点是让黄石公园出名的地方,因为关于它的标志性绘画(这里很“入画”)和照片(这里很“出片”)都是从这里拍摄的。从艺术家点可以眺望远方的下瀑布和两岸的岩石。黄石公园就是从这里获得了它的名字,因为这里的岩石是黄色的。这里的整片地方叫做Grand Canyon,亦即大峡谷。这里也许就是黄石公园最著名的地方了。
我现在感到遗憾,没有在那里多停留一段时间,更多地感受那里的震撼。康德喜欢谈论的自然的“崇高感”萦绕在我的心头。然而,旅行中的一大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身在壮美的景色之中,而且好不容易才能去一趟,却“身在福中不知福”。连续几天的旅游会让人逐渐失去对大自然的惊奇感,这种惊奇感可能只有在回忆之中才能真正出现。我仍然认为沉迷于拍照要对此付出部分责任。如果我们对着屏幕来看景色,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那里呢?
站在这里,自然似乎和艺术合为一体。我想起我在参观波士顿美术馆时进入一个巨大的欧洲文艺复兴绘画艺术画廊时的“升天”的感觉,我站在这里时也有类似的体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提升到一个相当纯粹的层次。



再一次,我们没有多做停留,而是前往下一个地点,泥火山(Mud Volcano)。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了一个水泥般颜色的正在不断沸腾的温泉,也看到了邻近的牛群。它们在安静地觅食。虽然有听说有牛攻击人的事情发生,但是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它们似乎也对人们不感兴趣。


下一站是叫西拇指(West Thumb),是位于黄石湖西边的一块地方。这里我们又有机会下车去沿着栈道多走一段时间,这里又分布有大大小小的喷泉。其中一个湖岸边的喷泉正在沸腾,而当湖水的水位线较高时,会把这个小小的喷泉给淹没。
走在湖岸边的栈道时,很容易碰上其他同行者,包括杭州的母女和小姑娘。大部分人都沉浸在拍照之中,而我发现小姑娘正在脱离这种趣味,而是走走停停并看起来陷入沉思的状态。虽然我不知道她在思考什么,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更高的状态。而大叔不同,由于他是一位专业摄影师,所以他关注于拍照是可以的。



接着,大巴车带我们去了大棱镜喷泉(Grand Prismatic Spring)。但是,再一次,我们去得太晚了,此时的光线情况已经不允许让我们看到它最为色彩斑斓的样子,而且它释放的巨大的水蒸气也阻碍了视线。同样地,如果要观赏大棱镜的全貌,更好的地点是附近山上的观望台,而不是走在这里面。奇怪的是,我注意到干涸的水池里被丢弃了一些帽子,不知何意。


然后是这一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彩锅泉(Fountain Paint Pot)。我们又有机会在栈道上走走,不过此时,许多人已经感到劳累了,而且天色越来越晚。而我自己举起相机的愿望也越来越低。我们来到Fountain Geyser附近时,这里的喷泉正在激烈地喷发着。泉水狂乱地从地下泼洒出来,连带着巨大的水蒸气柱。
此时,台湾大叔找到我,说他的妻子没有跟上,希望能跟我搭档拍照,而且许多人都已经互相结为搭档,我欣然应允。



这时我又遇到了小姑娘,她时而驻足观赏,时而走得很慢,时而走得很快,有时候会站着或蹲下来拿着她那个iPhone的Max型号进行拍摄。我想跟她搭话,聊聊她的旅行感想,但是错过或没有找到机会。俗话说,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timing(“天下没有完美的时机”)。一个人应该去创作好的时刻。
晚上我们回到了西黄小镇,我和大叔找吃的,又遇到了芝加哥大妈,我们三个又去了之前去过的中餐馆。事后查看账单,这家店的小费居然是强制收取的。
今晚似乎又有饮酒活动,但是我决定不能再喝了,我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既不舒服而且也很困倦。我买了一盒牛奶后,原本打算在房间里休息一会儿再去他们房间看他们喝酒和聊天。我去打了个招呼,看到又有新的同行者加入。但是我回到房间脑袋沾上枕头后很快就睡着了。等我再次醒来,已经是10月1日的早晨。我差不多睡了10个小时。
离开黄石国家公园
由于国会没有通过预算案,导致联邦政府有停摆的可能性,而这也会导致黄石国家公园关门。在这天早上我们知道危机已经解除。
这一天我的身体状况已经好转大半,基本上恢复了活力。这一天,大巴车的路线是从黄石公园的西门进去,南门出去,出去后便直接进入大提顿国家公园。这样,我们就还有机会在车上看黄石公园最后一眼。
中途路过了一个卫生间,我没有下车,许多人下车后,而回来的每个人几乎都在抱怨卫生间的脏乱差。由于美国景区的卫生间有时候供不应求,人们经常要排队,而且有许多是旱厕。谢天谢地,我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方面需求。Ethan提到,在国家公园预算不足的时候,卫生间根本就不开门,许多人在直接在卫生间外面解决了。也许它们可以提供更舒适而且自动化的卫生间环境。
路上的许多道路是我们前两天走过的。大叔开始跟我谈起,黄石公园里的植被非常单一,主要都是松树。如果公园里的植被多样性更丰富,它会不会更高,这真是一个问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片区光秃秃的,而它们显然是被野火烧过的。
Ethan说,为了给我们“加深印象”,决定给我们播放一个关于黄石公园的纪录片。它开始播放后,我发现视频的台标上赫然写着CCTV-10。在美国播放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感到非常奇怪,而且大叔也对此感到惊讶,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跟我共享这种感受。不过,这个纪录片显然也是引进和翻译的美国制作的纪录片。不得不说,纪录片里的黄石公园,似乎跟我们看到的东西区别很大。
在黄石的南门,Ethan让我们在门牌那里拍一张集体照。人们在下面做准备时,我发现小姑娘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地方休息,我几乎没有迟疑,径直上前搭讪:“你觉得这趟旅程怎么样?”这是一个在美国开启谈话的标准方式,不过我真的很想知道她的看法。
她的反应很快:“挺好的,就是有点累了。”
我说了声“啊”。
她接着问我:“你也而是一个人来的吗?”
我回答说“是的”。
接着,她询问了我的来历和身份。具体到了我现在是读博的哪一年,我犹豫了一下说“第四年”。
我问她从哪里来的,她说“罗德岛”。
我停顿了一下,问道:“本科?”
她笑得很灿烂:“我都研究生毕业啦,你觉得我看起来像还在读本科吗?谢谢啊!”
她这句话把我要说的话说完了。不过我并不是有意恭维她,而确实觉得她像是本科生。接着,她说自己很快就会回中国参加大厂的集中招聘,是上海人,等等。
现在,我心目中关于她的“画像”又具体了许多,但在消除一些神秘感后,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接着,我问她要不要帮她在门牌那里拍照,她想了想说“不用了”,因为她已经拍了太多照片了,也已经发过一些动态了。“拍了也不会发……难道你拍的每张照片都会发吗?”她问道。我说:“不用发,可以留作纪念呀。“
我的意思是,若干年后,我们总是会在各种偶然时刻看到自己拍下的东西,并构成回忆的资料基础。不应该只是为了发动态才拍照。
谈话到此结束,因为此时合影开始了。

她似乎很喜欢做出这样一种姿势:坐下,然后一只手臂向上,另一只手臂向下,呈现出迎风飞翔的动作。在拍完集体照后,我发现她一个人坐在河边正在做这个姿势,我迟疑了一会儿,看看是不是她在找人拍照,但发现没有后,我立即抓起相机,但已经晚了,她已经把手臂放下了。

导游在拍了集体照后,是如何把照片传送给大家的?谢天谢地,这个旅行团没有继承来自国内的一个恶劣的习惯:建微信群。于是,导游通过Airdrop传给了大家,而这旋即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这样的Android用户怎么办?无论如何,大叔在收到照片后,通过微信把集体照发给了我。
大提顿国家公园
在我报团的时候,我注意到行程表上有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但是它的游览方式仅限于在两个地方下车停留一会儿,则是我没想到的。与其说这是游览, 不如说是经过。
在车上,我们看到了河对岸的雪山,有些人要求停车下去拍照,大叔也说如果这都不让下去拍照的话会“惨不忍睹”。不过Ethan自有安排,他让我们在Oxbow Bend的地方下车了,这里是蛇河(Snake River)的一个蜿蜒处的河岸边,此时雪山已经被远远甩在后面。

正当我只能找到一些再寻常不过的取景时,别出心裁的大叔已经在旁边的公路上找到了更好的素材。他告诉我,这张照片既有近景,又有中景,又有远景。看来以后我得多琢磨琢磨。

在前往下一个停车点的路上,天色逐渐变暗,一边下起小雨,一边狂风大作。此时,大巴车内反而变成一个更舒适的地方,而不是外面。这个地方叫做Teton Point Turnout,站在这里可以俯瞰下面的河谷河远处的提顿雪山。下车的人们立马感受了绵绵细雨和号号狂风,于是很多人没待几分钟就上车了。北侧的山清晰可见,而南侧的山则笼罩在云雾中。下面的河谷看起来也赏心悦目,仿佛世外桃源。


走出大提顿公园的时候,有一个路段发生了堵车,原来是有辆车翻下了路边,但看起来事故并不严重。两位好莱坞音乐学院的姑娘有点焦躁不安。其中一人说“没信号,还堵车”,于是觉得现状很惨。许多人坐在车上就开始看手机或睡觉,但这样会错过外面的风景。
这样,大提顿公园就结束了。实际上,本次旅程的主要之点在此都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路上下起了大雨,好在抵达杰克逊镇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下雨。
从杰克逊镇到盐湖城
杰克逊镇有一个公园,这里有几道装饰性的门是用鹿角做的,于是这里也成为了一个景点。我发现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也就没有“打卡”拍照。Ethan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用来看这个公园并且吃午饭,他再一次带大家去一个餐厅,我一开始也随大流跟着大家走。这时我注意到小姑娘停在路边查看手机,她是不会放过自己探索这个小镇的机会。我们从她身边路过时,她又用那种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实际上,我也是这样的人,不过这次旅行我要比以往更注重社交性。

于是,大叔、芝加哥大妈和我又神不知鬼不觉走到了一起,我们先是进了一家牛排店,但是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牛排,于是作罢,找了一家披萨店。在吃披萨时,大妈继续向大叔讨教摄影。等我们回答大巴车上时,大部分人都已经到齐了,也许我们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拖了后腿。
从杰克逊到盐湖城便主要是赶路了,大巴再次在Flying J Travel Center停了一会儿,不过此时我已经感受到了告别的氛围。此后的路程跟前几天来的路程一致。此时,坐我附近的来自杭州的母女遭遇了一件麻烦事,她们这天晚上从盐湖城回到洛杉矶的机票买得有点早,导致她们有赶不上飞机的风险。
大巴要在大盐湖附近停一会儿,这两位母女径直下车打了个Uber前往机场——车费似乎由旅行社公司报销。而我们则下车游览一会儿。我以为这就是大盐湖,但这只能算一个水库,只不过跟大盐湖连通了。两位音乐学院的姑娘的其中一位,一走到湖边便说:“这还不如西湖,而且西湖是免费的。”
我们只能在湖边停留一会儿,而此时我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告别气息。此时是下午六点,阳光还好,但正日薄西山。于是我抓紧机会拍一下人。


我们只是在这里停留了十多分钟,因为其他人很快就上车了,我们也不好继续待着。看起来大家都开始感到有些厌倦了。
返回城内的路上,已经接近傍晚,我们在左边的群山附近看到了彩虹,它的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两道虹几乎跟地面垂直,我们可以凭借想象力认为两道虹可以组成一道完整的彩虹。彩虹似乎也在随着我们而移动。有一段时间,一道虹在左边,一道虹在右边,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从中间穿过去。车内的同行者们,尤其是一些大妈,对这一景象惊叫不已。她们至少还有对自然感到惊奇的能力。但由于车辆一直在运动,它很难被很好地拍下来。
告别
大巴把我们拉到了一个自助餐店。Sunny、Rex、曹先生和他的妻子则自己去觅食了。按理来说我也应该跟着他们去,但是由于我因为等会儿要在车里取行李走人,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我先跟他们告别了,Sunny用一口广东普通话对我说:“你多保重哦。”
大叔和Jay也没有时间吃饭,而是直接赶往机场。我先跟大叔握手告别了。如果没有他,很难说我会不会来这一趟。
吃饭的时候我和另一位上海大妈坐在一起,她虽然是三个人一起来,但是一个人住房间。我得知她这次从上海来是加拿大和美国都要玩,黄石这里玩完了还要去加拿大班夫看枫叶。虽然“中国大妈”这个词会给人带来一些刻板印象,但是我这次遇到的上海大妈们说话都轻声细语、心思细腻。
我吃完回大巴车取行李,在夜色中,我看到音乐学院两位姑娘和那位小姑娘已经取好行李往外走,准备到公路上打车。小姑娘只背着一个轻便的背包。我看着她,她也注意到我,她给我做了一个告别的手势,而我也做了同样的回应。音乐学院的两位姑娘则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我取完行李后,先跟司机告别,再跟路上遇到的返回大巴车上的其他同行者们告别,最后再跟Ethan告别。Ethan和我握了手,他很热情地说了再见,并祝我保重。
后续:在盐湖城的谈话,以及射击运动
离团后,我一个人在夜晚的盐湖城街道上走着,路上都没什么人。在我思考安全问题的时候,一位黑人在人行道上骑着摩托车跟我相遇而行,同时对我做出某种威胁性的手势后离开了。这时我决定直接打车而不是坐公交车前往我预定的Airbnb。
Airbnb的一个优势是它一般都会提供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我当晚把所有衣物都清洗了和烘干了。随后,一位在中国的朋友跟我视频,因为她要跟我直播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的婚礼盛况,不过我基本上没看清穿着婚纱的那位同学。同时,Rex联系我说第二天可以去一起“打枪”,这件事他之前也跟我提起过。一开始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担心这件事可能有些过于复杂,不过好在他一再推荐,我决定参加。
10月2日上午,我先打车到他们住的酒店的餐厅——他们实际上是今天离团——在这里跟Rex和Sunny相见。我其实没想到还会见到他们。我们在这里喝咖啡继续聊天,并且遇到了另一对我忘记名字的夫妇。男子之前在法国工作和学习,最近他们住在北京,在做某种远程的世界范围内的创业工作。
我和Sunny和Rex分别聊了很多。由于我对他们在西黄小镇的第二晚聊过什么很感兴趣,所以询问了他们这个问题。Rex的复述和总结能力非常好,让我一下子就很清楚他们那聊过什么。如果第一晚聊的是轻松的话题的话,那么第二晚他们就涉及到了严肃话题,并且很明显地出现了不同观点的碰撞。Rex也和我谈到了目前中国的不婚和生育困境,她注意到团里的几位年轻工作女性似乎都没有结婚。
Sunny则跟我谈到了中国历史从古至今缺乏变化——用黑格尔的话说,那就是“中国没有历史”——以及相关的关于中国未来的问题,由于她生活在香港,同时我也问了她对近些年香港的情况的看法。
我发现能够跟各行各业的精英谈论社会议题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虽然我在学校的时候也乐意听或参与这样的谈论。但是行业精英们毕竟有着真正的社会阅历和经验,并且明显站在一个比底层老百姓更高的观望台。
由于Sunny中午的飞机,她临近中午的时候坐车走了。而Rex、北京夫妇和我一起去“打枪”。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射击运动店,这里可以买枪、租枪也可以只是打枪。服务员听我们要打枪后,收走了我们的ID,随后给我们演示怎么操作武器,教了一遍并讲授一遍注意事项后,就把枪和子弹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走去下面的射击场。
我们拿了一把手枪Glock 44和一把半自动步枪Smith & Wesson M&P15-22,它们使用的是.22 LR子弹,这种子弹价格低廉、后坐力小且噪音小,但威力很小、射程很短,所以一般仅用于射击运动。
我们要戴着耳罩和护目眼镜进入射击场,而射击场里面也没有什么工作人员。我不得不感叹,美国人的心可真是宽啊,就这么放心地把这种杀伤性武器交给了从未碰过枪的人?进入射击场后,我不得不开始适应各种短促而巨大的噪声,显然,这种狭小的室内环境也大大加剧了噪声的力量。起初,我很容易受到惊吓,尤其是更大威力的子弹射击爆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
虽然服务员以为给我们讲清楚了,但是我把枪拿在手中时还是有一点慌乱,连忙持续请教Rex到底怎么用。不过,在成功射出第一颗子弹以后,我便开始适应射击。在扣动扳机时,我感觉自己处于短促的“失魂”状态,因为这种噪声就在我的手边爆发出来。步枪要比手枪好用,因为它的后坐力很小,扣动扳机后发生的事情很平稳。只需要把红点瞄准镜中的红点对准靶子即可,但似乎很难精确集中目标。
接下来,主要是在Rex的建议下,我们又去拿了更大威力的枪,把半自动步枪换成了FN 15(疑似),使用北约标准5.56×45mm弹药。我忘记了手枪的型号,但也换用了更大的口径。这样我们就能体验实战中的武器类型了。

这两种枪的直观感受时,子弹要大得多,后坐力更大,噪音也更大。尤其是手枪,后坐力会导致自己的手臂经历一个明显的短促的上扬。后坐力倒不是问题,而我还是对这种弹药的巨大的噪声适应了一段时间。我想起约翰·基根在《战役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和索姆河战役研究》中提到,中世纪的士兵很难想象现代战争这种巨大的噪声,而我现在算是对这种噪声有了某种直接的认识,而真实战场上的炮弹爆炸的声音或许更加震耳欲聋。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失魂”的感受也更加明显,以至于我只希望赶快完事。也许是因为步枪比想象中更沉重,所以打完一轮还有点累。幸运的是,我居然击中了一个10环。

不过,我感觉Rex和北京丈夫上手要比我快很多,他们也是第一次射击。Rex在用手枪射击时,隔壁的一位外国人向我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意思是觉得Rex的射击技术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行射击,尽管我已经忘记哪一年我开始玩射击游戏了。我也很喜欢狙击手这一角色,不过这次我们没有体验狙击步枪。
我对控枪这一美国议题持开放态度,这次实际使用枪支也并没有给我的态度带来明确变化。我确实感到我手中的武器可以带来危险甚至杀戮,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十分小心谨慎。但也许正是在使用过后,我对它也就没有了来自未知的恐惧。人一旦能熟练地操控枪支,那么理论上就不会把它用在不该用的地方,但真实世界中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同时,子弹爆发的巨大噪声所带来的“失魂”感,似乎跟战场上甚至犯罪时短暂地失去人性甚至以杀戮为乐的极端情况有联系。
我们在射击时,也遇到一家人,丈夫、妻子和几位很小的孩子进入射击场来射击,并且她们显然在使用快速连发的自动武器。那位妻子在射击完毕后跟我眼神接触,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她友好地甚至有点害羞地对我发出了笑容。很难想象,她刚刚才在射击场内用自动武器射出许多子弹。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射击就是一种家庭娱乐活动。
不过,这次经历也没有给我带来想要再次尝试的欲望。也许试一次就够了。
离开射击运动店后,他们三人要打车回酒店取行李然后去机场,而我则决定利用剩余不多的时间在盐湖城市区逛逛,再回我的Airbnb取行李。于是,我跟北京夫妇,以及让我印象深刻的Rex,分道扬镳了。
离开盐湖城
我径直打车去了犹他州议会大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其实都极少打车,而是靠公共交通和走路。但是人在旅途,要赶时间的时候必须要打车。


犹太州议会大厦这个建筑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新鲜感。我开始怀疑是不是美国所有的议会大楼都采用了这种新古典主义风格。不过我没想到这里是可以走进去参观的,甚至几乎可以去往除各个具体房间以外的任何地方,负责安保的人也寥寥无几。我也参观过国会大厦,但在那里,许多区域是不能去的。州长、州议会和州法院都在这座大厦里办公,不过在我们参观时,我似乎没有碰到任何在这里工作的人。
随后我徒步向南走。由于我的时间不多,得像参加旅行团一样火速把这里的主要东西看一遍。我先找了家快餐店吃午餐,再去了马德琳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Madeleine),从街边推开大门就进去了,而里面正在举行宗教活动,我也就不好进去参观。只是站在门边往里面看了看。我在前往教堂的路上,在等一个红绿灯时,旁边也有一位黑人女士在等,她主动找我搭讪,问怎么样,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这里,觉得盐湖城怎样,等等。我开始惊讶这里的人的热情程度。
我一开始还在想这是不是个案,不过后来我又遇到好几对在胸前佩戴国旗徽章的年轻人热情地对我打招呼,有好几个人佩戴的是欧洲国家的徽章。由于我正走在摩门教总部——准确来说,它应该被称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附近,所以我理所应当地想到,她们可能是跟摩门教有关。后来我查询资料发现,确认她们应该是摩门教的传教士。由于摩门教的标志性建筑正在维修,而我也得赶时间,所以我没有仔细参观这个地带。
我坐公交车回到Airbnb取到行李后,再前往机场。在进入机场时,落日的余晖正照耀在远处的山峦上,而且山峰上覆盖着雪。在安检处的外面,我把带不走的两瓶没开的饮料送给了一位清洁工。同时,我看到一对情侣也在外面拥抱和亲吻,他们都哭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场景令人动容,而且路过的另一个人也对他们说:“Oh, you are so cute.”(你们真可爱啊)虽然我以前也见过机场或车站的告别,但如此戏剧化的告别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美国不愧是浪漫爱情的发源地。
他们终于分开了,男生噙着眼泪走向了安检处,而女生则停留在原地看着他。这时,我也走了进去,准备坐上前往西雅图的飞机。
结语
我的黄石之旅——我的旅行计划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此后我去了西雅图(包括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和雷尼尔雪山国家公园)和芝加哥,还去麦迪逊拜访了一位朋友。旅行后面的部分,我可能不会再写下去。
那么,现在如果要把我询问小姑娘的问题抛给我自己,我会如何回答呢?实际上,几天前,Sunny也这样问过我。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便是写出了这篇冗长的游记,但其实我还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去年,我经历了一个社交的转向,于是顺其自然地,这次跟团旅行的社交性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无论是接触较多的并且互留联系方式的大叔、Sunny、Rex,接触较多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的曹先生、Jay和芝加哥大妈,接触较少但我注意较多的小姑娘,接触较少的音乐学院两位姑娘、上海夫妇、上海大妈、杭州母女、北京夫妇、儿子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父母,以及导游Ethan和司机,以及其他我在本文没有提及的人们,他们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为什么会这样?我要先引用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的最后一句话:“在研究美学这个共同目的上如果你们和我已建立起一种联系,而现在就算结束了,我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美与真这种较高的,不可磨灭的理想的联系,把我们永远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与之类似,既然我们游览的是黄石国家公园,那么这种独特而壮观的自然之美也给同行者们带来了一种理想的联系,至少是给我自己带来了这种体验。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至少在华人圈里,同行者们都“素质”较高,这也给社交带来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我的感受也不全是积极的,不然这也过于天真。我依然感到华人的社交性相比美国人有明显差距,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总是给我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如果你在美国找异性搭讪,你可能只是才说了个Hi,对方就已经和颜悦色地主动迎上来了;但在中国,如果不是处于一个“完美”的时机,搭讪可能会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提防心很重,也可能是目前中国的性别困境的一道缩影。所以,在这次旅途中,我发现大叔和大妈的社交性最好,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只要能突破提防心这个最初的屏障,中国人也是善良的。
社交是跟团旅行的一部分,这甚至可以是它相比于自由行的一个优势。当然,跟团游的劣势也很明显,压缩的时间表、不停的赶路、几乎没有静下心来沉浸在自然,等等。所以,在跟团游的时候,趋利避害,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交,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心态。但是,也不要让社交耽误自己对自然景观的沉浸。有害于这种沉浸的,还包括互联网和摄影。拍照和分享的确很重要,但最好是拍完照后赶快沉浸在景观之中,并在观光的间歇期来编辑和分享,不要让它们耽误自己的旅行。
我对同行者们对此次旅程的感想和体验知道得并不多,所以这篇游记只好记述我自己的体验,以及我所感受到的他们。
到此为止,我还没有提及黄石公园本身,但现在也很难说点什么。Ethan提到,许多人在来过黄石公园后,在某个时刻会想念黄石公园,又想去了。黄石公园的确是我去过的自然景观中在我心目中名列前茅的,我相信那里的图像会持久地在我的脑海中发生停留,而不仅仅是在我下次旅行时看到类似景象时才想起它,并对身边人提起它。它的意义不在于我可以告诉别人我来过这个地方,而是一种对我的生命的持久的微妙影响。自然景观不像书本,它不会教给你任何东西,而只是让你用精神去感受。
也许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