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我不知道在何处读到了微信公众号changsview的文章《为什么唐山事件后某些男性发言是令人恶心的》,然后看到了作者列举了三种“令人恶心的”的发言,其中第一点是:“不承认男性有性别优势和特权”。这诚然是一种很常见的女权主义的观点,由于我当时正在阅读神经科学领域内的自由意志问题方面的书,所以当时我仅就这一点非常随意地写下了很简短的评论(我后来就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所以我已经删除了评论),以供博主考虑。其实,我在写下它的时候压根没想到唐山事件:
“不承认男性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权的一个原因是,这与自由意志的原则相违背。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男人一出生就有了道德负债,毕竟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很快,博主对我的评论进行了回复:
“所以女性主义并不是教人负罪,而是要教人反思。婴儿长大了会意识到整天哭哭啼啼要奶喝是不对的,但他要做的就是像个正常人一样自己吃东西,我们并不要求他为自己曾经是个孩子而负罪。”
看起来博主好像同意我的观点。当时我没有跟进回复,后面便很快忘记这件事。
现在时隔一年多,我刚刚惊讶地发现,博主又饶有兴趣地写了一篇新文章《唐山事件一周年:对“歇斯底里”的最新想象》,重提这件几乎已被忘却的事。而且这篇文章看起来是一篇正经的且精彩的学术论文,文风坚硬,雄浑有力,还很认真地做了引用注释,我必须佩服博主对写作的认真态度,正是这种专业精神引起了我继续交流的兴趣。
博主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三个人对他的评论作为例子——其中包括我当时的评论——来说明当下的“厌女症”,对女权的“歇斯底里”和“应激障碍”。时隔一年,博主似乎改变了看法,对同样评论的回应方式变得更加激进、更有攻击性。这里我们引用一下博主对我的话的评论,其中的加粗是我加的,我觉得这些说法特别有意思:
这一辩护是非常别扭而且在逻辑上错误的:他预设女性主义对于父权制的批判等于让男人自出生始就背上某种道德负罪感,仿佛女性主义对于男权社会的描绘是一种类似于基督教原罪观一样的、强加在男性身上的虚构。其次,他还预设了一个女性主义并不(一定)承认的主张,即出于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男性应该对自己的性别地位抱有“忏悔”一般的情感。
事实上,这类观点在男性异性恋共同体中相当常见,它基本上是一种部分男性对于“女权”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在许多次的公共事件讨论中,由于性别议题本身和双方立场的复杂性,女性主义的声音往往被掩盖在简单“喊打”的呼声之下,而这样的讨论场面到了部分男性眼中,则构成了一副荒诞的图景:原本与自己“无关”的社会问题被“强加”到自己身上,自己从社会事件的旁观者甚至批判者,一下子转变成为了“共犯”、“同谋”。这样的言论冲击,使得许多男性面对女性发声无法沿着其发言的合理性内核对父权制本身进行真正反思,反而由于在最原始的情感冲击中自动走入了与攻击者相对立的立场而进一步迈向了替父权制作辩护的道路。这时,他们才真正踏入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笼罩之内:因为正是当主体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持的意识形态时,意识形态才充分而真实地起作用[3]。
当我们回溯式地重构男性异性恋共同体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在类似的场景中迈入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笼罩时,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固定的模式,即:缺乏同理心与共情基础——在无共情基础上,受到女性主义立场的冲击——对女性主义立场形成误解和抵触——自我拟设为女性主义立场的“敌人”——通过加入对父权制的辩护成为女性主义立场的真敌人。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她的中文或英文教授的话,这应该可以给一个A的分数。老实说,我极少就性别社会议题跟帖,而一年多以前在那个公众号留下的评论可能是唯一一次,恰好又遭遇了如此认真的回复。
趁着这个机会,在这篇文章中我会更宽广地探讨“男性特权”说的两种回应,以及当下我们面临的社会心理困境。关于这个议题的街头辩论,可以参考Steven Crowder制作的相关视频。我自己对“性别特权”这个话题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说,我愿意听取各方面意见,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但始终要注意,“性别特权”这个命题是相当抽象的,以至于辩证的双方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尝试证明它的存在或不存在。
与博主不同,性别议题并非我的主要智识兴趣。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谈论这些话题——某些时候还得有意识地回避。生活和政治毕竟是两码事。而且我感到性别议题在现在差不多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第一种回应:男性特权是存在的且价值中立的
我要提到的第一种回应是,承认性别特权的存在,但否认它的价值性,同时强调问题不在于特权或权力本身,而在于如何把它运用到好的方面,或者值得它。据我所知,这种回应方式主要来自心理学家,由于心理学相比各种社会科学更接近自然科学,所以他们不太在意许多事情是否有价值性,而是强调客观地去认识。
不过,科学家们很少用“特权”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术语似乎已经自带价值判断了。毕竟,“特权”本来就应该指的是少数人的特权,从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说,人们不能说占人口一半的人拥有某种“特权”(privilege),而只能是“权力”(power)。
乔丹·彼得森似乎没有否认存在白人特权,但他也指出,拥有特权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拥有特权的人是如何使用自己的特权的。他说,有更多的权力,那么责任也就越大,“你需要更努力工作来值得它”。(比如,比尔·盖茨和马斯克这些人是不是把自己的钱用在了好的地方?)同时他也认为这一指控非常危险:“你可以用集体犯罪的方式来对付一个种族群体,而不管这个群体中的具体成员是否有罪,绝对没有什么比这更种族主义的了,这绝对是令人憎恶的”。彼得森在其他场合还说,他认为某些差距是有改善空间的(比如收入的差距),尽管可能无法完全相等。他也曾经否认“男性特权”这一说法,认为这是个神话。关于彼得森就“特权”问题的详细阐述,可参见2018年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身份政治与白人特权的马克思主义谎言》。
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亲密关系中的权力的存在并不是件坏事,而问题在于权力是否用在了好的方面,也就是运用在了维护亲密关系并使双方更加幸福上面。由于《亲密关系》是一本文献综述,所以它应该能代表心理学家的流行看法。米勒还尤其提醒那些相信权力本身是件坏事的人要“赶快”改变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提到了以下事实:实际上没人知道完全性别平等的亲密关系是怎样的,而试图共同执行性别平等的伴侣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很刻意、尴尬而不自然的处境之中。米勒使用的词语是“权力”而不是特权,很显然前者是中性词。不过,在亲密关系中,有时候是女性拥有更大权力。
进化心理学对男性特权的非价值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来自科学的论证。我们在人类的近亲动物中、原始人类中以及现代的原始部落中都发现了男性特权的迹象,它们已经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行为模式,以至于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所以今天依然有男性特权现象,实属正常。如果没有的话,反而是不正常的。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巴斯有一次提到,有次讲座后,有位女士向她抱怨说,他应该隐瞒他的发现,因为它会给女性制造痛苦。然而,科学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对他们来说,事实虽然残酷,但这的确是事实。
我不清楚女权主义者们是如何看待这种回应的,但很显然它暴露出了一种很深的歧见。男性特权是一些女权主义者痛恨至极的东西,但是这些人居然满不在乎地说:“啊,男性特权?确实是这样,这又不是坏事。”他们描述男性特权就仿佛描述地球在围绕太阳转动一样。
赞同性别特权存在的心理学家一般也认为,这种性别特权是无法消除的,因为这里面有某些根深蒂固的生理因素或人格因素。这意味着,任何试图取消性别特权的尝试都是徒劳的。
第二种回应:作为个人的男性对男性特权并无道德责任,对男性特权是否存在持悬置态度
第二种回应是我已经略微提及的自由意志理论(我想到的是康德),从这种理论出发,由于男性实际上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性别,那么他们对随这种性别而来的各种东西都是没有道德责任的。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人们才能评判这个人的行为是否是道德甚至是合法的。这种自由意志理论很显然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道德与法治的观念基础,从而是现代人的共识。
不过,从自由意志理论出发来进行的辩护,实际上并未否认(但可能也未承认)男性特权的存在,只是撇清自己跟男性特权的关系,这意味着自己身上没有男性特权的体现。举个例子,有个人对一个男性说:“你为什么不放下你的男性特权?”那位男性可能会说:“这是我能选择的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意思是,他既没法选择自己能拥有也没法选择自己能放弃这些特权,而且对这些特权也没有任何道德责任,同时也强调了自己具有独立于父权制的能力。
由于每一个男性并不是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性别,那么不管他出生在古代、中世纪还是现代,出生在哪个文化中,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事实都无法跟道德扯上关系。就算是一个人出生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儿子,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出生在显贵家是如此,更不用说寻常百姓家了。
拿现在美国的种族议题来说,现在的许多白人对自己的肤色感到很不自信,甚至有自卑感。这种情况有点像德国人的历史负罪感,他们由于纳粹时期的历史原因至今很难表现出爱国热情。可是,第一,无论是现在活着的美国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至少绝大多数都是在奴役黑人或大屠杀时代之后出生的;第二,虽然可以批评他们做得还不够,但至少一些美国白人和德国人的确也很努力地偿还历史债务,有时候甚至——用博主的话来说——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当然,现在离那段历史还比较近,但再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更有理由认为美国白人和德国人应该摆脱那种不自信感。
当然,无论是一年前的回应还是最近的回应,博主不认为女权主义想要让男性负有道德负债,至少自己不这么认为(博主无法代表其他女权主义者)。更为精妙的是,博主认为,一些男性指责女权主义者是想让自己负上道德债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陷入了面对女权的“歇斯底里”。
博主对“歇斯底里”和“应激障碍”的心理推定的修辞可谓相当精彩,但并未对这种推定提供证据。我作为一个文科生,也广泛参加校园社交活动,但遗憾的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女权主义者却是寥寥无几——这一点我也很震惊——至于博主描绘的这种热衷于在网上跟女权主义者进行政治辩论的男性,更是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也无法提供任何一手资料证明博主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了解过许多身边人的看法,包括同情女权的学传播学的研究生女性朋友,他们的反应可以这样来归纳:对女权主义许多言论感到匪夷所思,总体上不太关心。他们觉得爱更重要。他们大多数人都在谈恋爱。
我偶尔逛逛浙大的校内论坛,老实说,我感觉互联网上的性别战争在这里似乎并无体现。有一次,我看到有个人发帖嘲讽豆瓣上的厌男贴,有位女生回复:“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垃圾上面呢?跟朋友出去玩、谈恋爱不是更好吗?”所言极是,现在许多人在网上花费太多无意义的时间来争辩这种已经完全失去边际效益的话题了。男性特权这个话题即便在美国也相当有争议,出于这种观念冲突的必然性的情况,我觉得掉进无休无止的性别意识形态政治辩论对生活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也从来不介入政治辩论,也很少看那些东西。但我偶尔会读像博主写的这样有理论思考的东西。
那么,男性作为个人否认自己有道德负债,是否导致了跟“父权制”的“共谋”呢?“共犯”“同谋”这些字眼显然必须是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男性意识到要维护“父权制”并且去做,这样的指控才能成立。就像一个小孩点过年放鞭炮,却不小心引燃了整座房屋,我们不能说这个小孩有意识地要烧毁整个房屋。所以,博主的意思应该指的是“不自觉的共谋”。根据康德的道德学说,人们不应对非自觉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毕竟他们根本就没去意愿那件事。然而即便从后果的角度来说,我也没看出,如果一个人否认自己跟某件事有瓜葛,是如何导致,这个人在无形中还是参与了这件事的——如果这里的因果关系要成立的话,这里面恐怕还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才行。
当下的社会心理困境
博主虽然同意男性的确没有与生俱来的道德责任,但是男性自己说自己没有道德负债(这意味着撇清自己跟男性特权的关系),那这就是故意跟女权主义唱反调的表现,并且跟父权制沆瀣一气。也就是说,虽然那是对的,但是男性自己不应该这么说。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博主的论点虽然在表面上有点滑稽,但的确体现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某些社会心理。
这一怪现象实际上也出现在前面我所提到的美国白人和德国人的例子中。虽然现在的主流意见认为他们不必具有道德负债(it’s OK to be a white person),但是如果这些人自己把它当成口号来喊,对其他某些人来说,就好像是被冒犯了。这也是很多人指责日本人对二战反思不够的原因,尽管这件事基本没有损害今天日本的国际形象。虽然这里涉及到的是历史责任,而非性别政治——不过性别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历史性因素——但道德负债的认定却是很相似的。
把彩虹旗挂在伦敦街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同样的规模宣传异性恋,似乎就是一种压迫,从而是不合适的。最近几年美国大学男女比例严重失衡,4:6,越来越多的白人男性不上大学,许多大学招生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承认不敢对此出台什么特定的帮扶措施。于是,事情的唯一解决方案似乎是,非白人男性群体形成某种共识,团结起来要求大学改善白人男性的入学情况,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虽然某件事情的确是被接受的,但是对一些当事人来说,却不宜公开宣扬。骄傲的权利不属于这些人。
每一个现在的白人都要为白人的集体历史责任负责;每一个现在的德国人都要为德国的历史责任负责;每一个男性都必须必须为“父权制”或者“男性特权”负责;他们没有逃脱的权利——当然,这些观点在今天差不多已经被放弃了,但是它以更温和的形式继续存在:他们作为个人可以不用负责了,但是他们不应该自己去倡导这件事。这或许是因为,一旦个人开始倡导,那么必定形成集体行为。于是,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便开始分裂,这也就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
就这一问题而言,我是站在自由意志的立场上。我认为,无论是种族议题中的美国白人,历史责任议题中的德国人,考虑上大学的白人男性,还是性别政治中的男性,他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尤其是表达自信,只要这些表达本来就是合乎常规道德的、没有冒犯他人的尊严、没有直接冒犯少数人士(比如在伦敦街头挂异性恋旗帜可能永远都不合适)、没有冒犯历史上的受害人及其后裔,那么就跟道德无关,也受言论自由权的保护。如果我们的时代不想继续沦陷在这诡异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心理氛围中,我们便必须迈出这一步,而且这也是迟早的事情。男性出于自由意志,否认自己作为个人拥有性别特权——这仅仅意味着否认自己跟男性特权有任何瓜葛,而不是否认男性特权的存在——便是处于这一范畴之中。
结语
最后,作为一个精通心理咨询理论的人,我想说,博主几乎肯定是在滥用“同理心”“共情”这些概念(这两个词其实在英文里是一个词empathy),因为这些概念要在非常具体的沟通情景中才能运行,而根本无法在抽象的两性关系、种族关系中施展。我已经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回应了女权主义者这种常见指控。至于“歇斯底里”和“应激障碍”,当然就纯属术语滥用了(尽管博主非常清楚DSM-5里不存在”歇斯底里“这个术语),或者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我只能看作是目前中国互联网上的性别战争的常见表征(因为在性别战争中这些词汇也被用来描述女权主义者),无法真的相信它。
博主还反复提到一个对我来说相当新颖的说法“男性异性恋共同体”,我每次读到这个词都会发出一阵尴尬的苦笑。博主可能对生活中的男性知之甚少。诚然,我不认识任何参加性别战争的男性,但要说在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个共同体,那实在是天方夜谭。男性异性恋可能是所有人群里最不可能形成共同体的。戴维·巴斯在《欲望的演化》中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已经对同性竞争和异性合作进行过精彩的分析。之前我在浙大校内论坛看到有个人提到这样一个观察,男性不太倾向于像女性那样在网上拉帮结派,无法联合成一股力量——我认为这一观察更符合实情。毕竟,在中文互联网上,男性群体之间不存在那此起彼伏的“家人们”“姐妹”之类的称呼的对应物。而且如果了解当今时代的男性友谊现状的话,会发现年轻的男性异性恋群体是当今孤独比例最高的一群人,最近几年已经有许多作家在讨论男性友谊的衰退(Friendship Recession)了。有趣的是,关心男性友谊衰退的作家们有很多是女性,而且跟女权主义没有关系。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回应,不如说是对相关话题的更进一步说明。期待能为更多思考此类问题的读者们带来一些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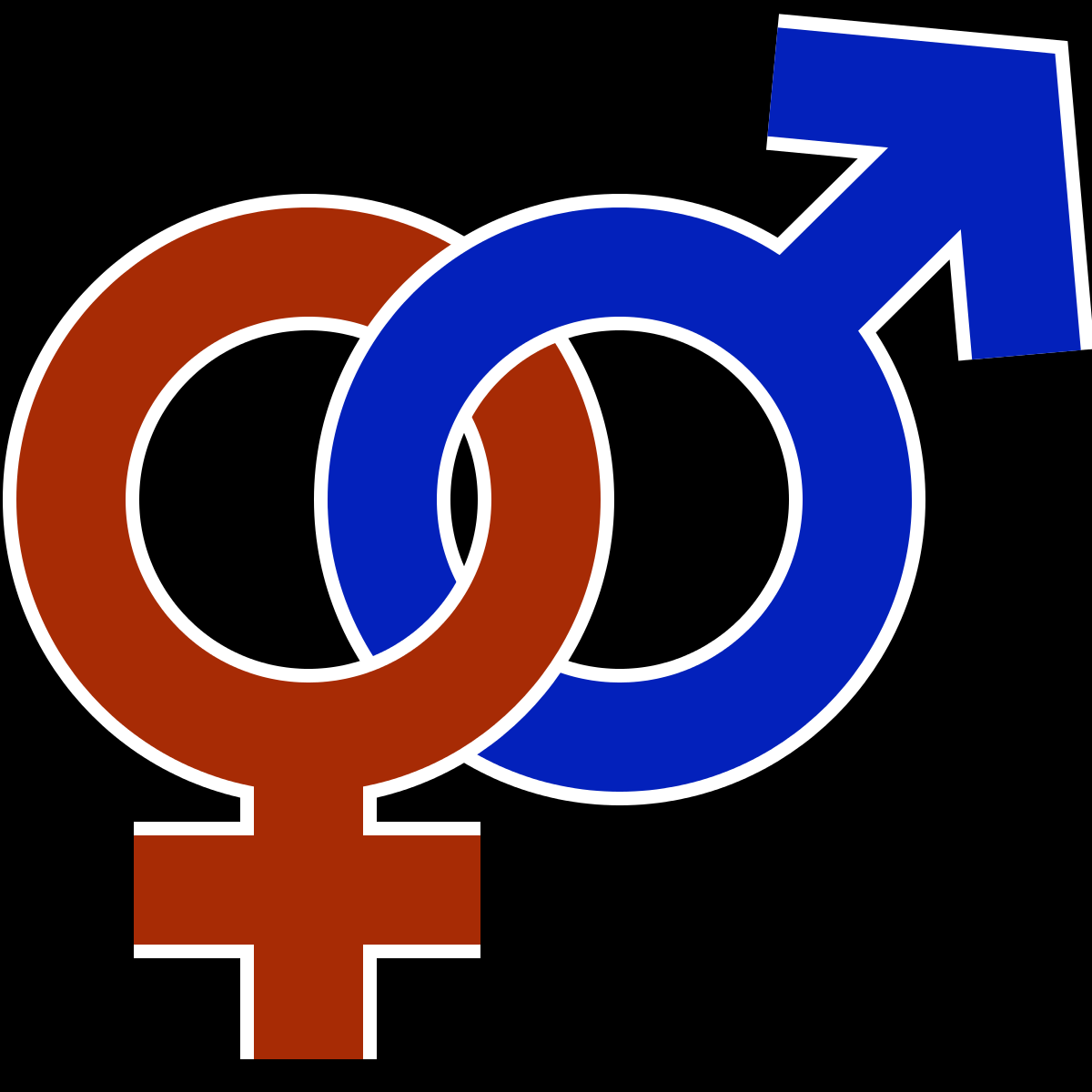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