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格尔哲学以来,客体化、物化、对象化、异化等之类的概念便成为各种激进理论或批判理论的基本概念——而这诚然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在黑格尔那里,“客体化”这一概念是一个中性的和良性的概念,它是自在自为的主体确认自身的必要途径。
我们这里谈一谈“性客体化”。当我想到这个概念时,首要反应是康德对婚姻的定义,他认为婚姻是两个人互相利用对方性器官的契约。黑格尔认为这个定义“实在是拙劣出丑”,他认为浪漫爱情才是婚姻的核心。显然,康德至少在对婚姻的理解中进行了性客体化。什么是“性客体化”?为保险起见,我借用一个能得到广泛共识的定义:性客体化是对性伙伴的物化,即把他们看作是性对象,以及他们的性属性,而不适当地承认或尊重他们作为一个有自己的情绪和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遗憾的是,大约两百年后,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继续对婚姻采取了康德式定义,这个按理来说应该反对对女性进行性客体化的人却反而在大搞性客体化。

我想起许多年前,那是小时候,一个深更半夜,我坐在一辆长途黑车里,两位男士旁若无人地聊起了嫖娼的话题。几年前在西藏旅行的时候,一位中巴车司机兼导游一边在西藏的美丽风景中疾驰,一边对全车乘客聊到,他的妻子允许他嫖娼,还给他钱去嫖娼,因为身在异地的她无法满足他的需要,而她知道这只是一种“交易”而已。
现在我回想起来,可以肯定,那些人在言谈中把性工作者“性客体化”了。然而,这只是公开的层面,很多性客体化是纯粹在心灵世界中进行的,而这样的现象在男女两性中都是存在的——简中网友只需要多在豆瓣之类的地方多逛逛就知道了,因为某些心灵世界的性客体化表达在了这样的网络论坛中。
没有性幻想的人应该是罕见的。如果我们不进行性幻想,这说明身体机能出了问题。然而,如果我们对一个人进行性幻想,但是对那个人不投入什么情感,那我们就是对那个人进行了性客体化。性客体化在人的心灵世界中的某些时刻同样是很常见的情况,只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把它表露出来。根据一项调查,女性的性幻想中,27%是明星,39%是陌生人,在这两个类别中女性比男性进行了更高比例的性客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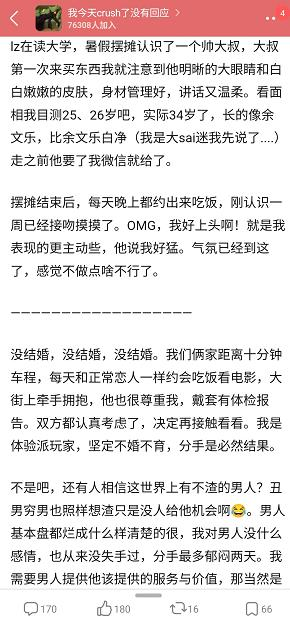
那么,性客体化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像一些女权主义者所诉诸默认的那样,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要如何解释女性对男性的性客体化呢?实际上,当女权主义者把性客体化和性别不平等捆绑在一起,便是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一个巨大的谎言。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参考的是扎实的实证研究,而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夸夸其谈和天马行空的想象。Blake, Bastian, Denson等人于2018年在《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发表了一篇论文《收入不平等而非性别不平等与社交媒体上的女性性化呈正相关关系》(Income inequality not gender inequality positively covaries with female sexualization on social media)。这篇论文使用的概念是“性化”(sexualization),它研究的是Twitter和Instagram上许多女性发布性感自拍的现象。论文作者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性别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社会中,性化程度的上升是最明显的。他们发现,性感自拍相对较多的地区在经济上更不平等,但没有更多性别压迫。他们还发现,美国经济不平等(而不是性别压迫)的地区也有更大的与女性身体外观提升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美容院和女性服装)的总销售额。文章的结论是,性化表现为对经济条件的反应,但并不与女性的从属地位相关联。他们还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性化可能是妇女社会地位攀升的一个标志,它跟踪当地环境中的地位竞争程度。
这篇文章研究的是女性对自己的性化,这跟“性客体化”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女性的性化就是她们对自己的性客体化。性化和性客体化几乎是一回事。由于女性对自己的性客体化是在女性之间进行竞争的表现,那么她们便主要是为了获得男性的关注。于是,女性对自己的性客体化与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便构成了一个循环。询问“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很明显,文章提供的结论也可以用来理解与性客体化相关的所有社会现象,包括情色行业。在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女性之间的竞争激烈,而这种竞争表现为女性的性化,即女性对自身的性客体化。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表明,性化和性客体化跟性别不平等是没有关系的。在性别越平等的地方,性化和性客体化更明显。作者提出的猜想也值得注意,性化正好是女性社会地位攀升的一个标志。但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个现象从一个方面验证了“性别平等悖论”,即性别越平等的地方,性别差异越大。
当然,也许一些女权主义者还会继续争辩说,虽然从经验上看性别不平等与性客体化没有相关性,但是它们在哲学上是有关系的。
第一,她们或许认为,女性居然要通过发布性感自拍来相互竞争,而男的需要吗?这里的问题在于,这些人把性别差异理解为了性别不平等。最近若干年的研究显示,在性别越平等的地方,性别差异也越大,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情况,而这也预示着人类社会的未来。
第二点,她们或许认为,女性是性客体化中的客体,而男性是主体,主体通过构建客体来维护男权制。这里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女性的性本能,忽略了女性的主体性,尤其是忽略了现代世界已经打开了女性的性潜能。这些女权主义者似乎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当她们发现女性在前现代在性方面是受压抑的并且现在已经获得解放时,却干脆沉溺在过去的困境不能自拔,继续声讨女性被性客体化。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男性和女性同时是主体和客体,他们取得了相互承认——而这本书出版于1807年。两百多年过去了,现实不知道有多大进步,而我们的理论却在退步。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居然还在鼓吹“女性是客体,男性是主体”的陈旧得掉渣的理论,仿佛这个世界在这两百年变得更糟了一样!
第三点,她们或许认为,这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共谋”。这里的问题在于,对社会体制进行拟人化的阴谋论在科学上是行不通的,这里很显然陷入了一种非形式谬误,甚至答非所问。即便真的存在这样的阴谋,那这也只能说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试图通过加强性客体化来实现性别不平等,但这条通路还没有得到证明。性客体化——只要停留在人的心灵世界而不形成一种社会体制性的东西——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幻想,就不可能导致性别不平等。
很多时候,一些事情使得一些男性对女性的性客体化造成了实在的影响。性骚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或其他更可怕的事情)。当然一个人只要对另一个人投入了真实的情感, 进行性骚扰的可能性就低得多。比如,假如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么就不太可能对她进行性骚扰。
女性自我性客体化也加剧了(不是造成了)女性的容貌焦虑。最近我听一位同学说,她如果早上不花个半小时时间化妆都不敢出门。但要注意的是,女性想要提升自己的性吸引力或外表吸引力,这究竟是一种天性还是性客体化,并不容易区分清楚。如果一位女性在化妆或整容后,站在镜子面前,感到那个自己多出来的或修改的部分,完全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在我看来,那似乎不算是性客体化。但是当一位女生怀疑每天花半小时化妆的意义却又“不得不”做时,那显然是性客体化了。要缓解容貌焦虑并不容易,而这主要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不是社会学问题。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提出“性客体化”是导致浪漫爱情危机的一大因素。韩是在所有性别上使用这个词的。从哲学上来看,也许吧。但从心理学或真实世界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心理学界最近一些关于男性观看色情制品的研究,既没有找到它加剧了性客体化的明显证据,也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其他明确的消极影响。认为观看色情制品影响了男性的生活健康,这一观点似乎有些武断。当然,男性最好还是不要沉溺在色情制品里面。
总之,性幻想是人的天然活动,性客体化作为性幻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样是中性的。假若性客体化表露出来并侵犯了一个人的尊严,无论是通过言语还是行为,那这理应受到谴责或得到惩处。同时,女性的容貌焦虑也是一个潜在的心理问题。性别不平等是存在的。但在现代世界,没有迹象显示性客体化导致了性别不平等,或性别不平等导致了性客体化。性别不平等的确为性客体化提供了一个背景,但它们没有相关性。正如“性别平等悖论”所揭示的,随着性别权利继续趋于平等,性客体化以后只会多,不会少。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做一个社会化的人把它限制在心灵世界的一个角落里。
发表回复